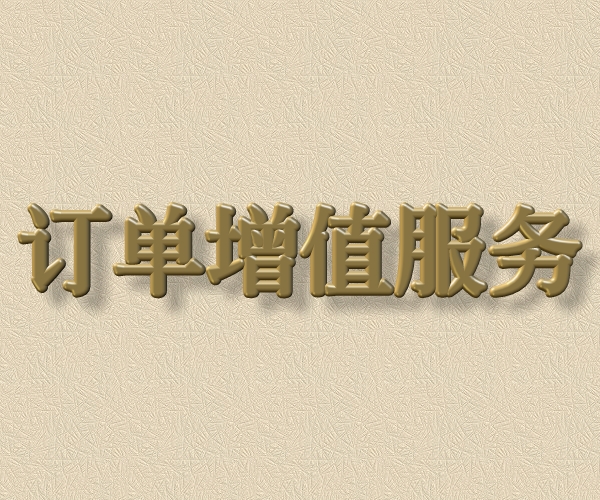| 返回 |
从开放社会到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罗永生 自从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以来,索罗斯(GEORGE SOROS)的名字在香港突然变得家传户晓。报章不仅连篇累牍、图文并茂地把索罗斯描塑成国际金融投机者的代表、亚洲经济危机的始作佣者,甚至痛骂他为“金融恐怖分子”,就好像狂魔现世,撒旦重临。亚洲神话的急速破灭,对不少在过去十多年来,参与建构这个新兴工业国奇迹话语,以至被卷进去的人,至今仍然是一件“不可理解”、“难以致信”的事。不但经济理论家无法自圆其说,一般民众更是不知所措。在这情况下,一个高度漫画化、妖魔化的索罗斯形象,正好提供一种心理解脱,给予亚洲资本主义奇迹的早夭一个便捷的答案。早在一九九八年初,泰铢贬值风潮之前,在香港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年会上,索罗斯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进行公开论辩。当时索罗斯已多多少少被定型为西方国际资本主义的代表,而马哈蒂尔则被归类为那些勇于颂扬亚洲价值的政治领袖,为有别于西方的亚洲兴盛模式辩护。有趣的是,不少从前是非西方、反帝国主义的辞令,在这项新的关于东西文化竞争的话语建构中,不再是被运用来针对一个敌对的体制,甚至不是用来批判强权国家,而是被转移到一高度个人化的形象身上,仿佛资本主义就只是进行个别投机活动的金融大鳄一样。 毫无疑问,索罗斯身为国际最负盛名的对冲基金投资者,对马哈蒂尔所希望代表的所谓亚洲经验大不以为然。然而,如果我们只懂得使宜地为危机找个替罪羔羊,我们将会失去认清问题的机会。特别是这次金融风暴的背景,正是全球化历程已进入一个全新阶段的时候。简单地把索罗斯妖魔化,往往会同时使我们忘记了,无论是在这次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中举足轻重的对冲基金,还是所谓亚洲新兴工业国经验,其实都是在全球化这个相同语境下才会出现。当全球化的进程从提升几个民族国家或区域的国际城市跻身先进行列,推进到要瓦解民族国家的界线、壁垒,将它们都抛掷到全球市场的大风大浪里去,我们就更不能只顾如何梦想分享全球化的成果,而忘了去了解全球化的真正意义。又或者简单以为,亚洲发展模式,已是一个民族国家抵抗西方殖民支配的最后希望。或者,在刻板化的东西方对垒的表象背后,我们需要的是深入而具体的分析全球化浪潮。只有从制度到价值的不同纵深面上考量全球化,我们才能了解民族国家的作用,或者亚洲经验的意义。恰巧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难发觉,索罗斯虽然是一个全球金融一体化的重要参与者,而且在多次的全球性金融炒作中得利,然而他却不是毫无保留的全球化鼓吹者,相反地,他对全球化的认识和批判.往往要比他的论敌来得深入和彻底。要了解这个表面上互相矛盾的现象,我们不得不从另一个面貌的素罗斯说起,不得不去了解一个作为思想家,而非纯粹是金融投资者的京罗斯。 索罗斯是匈牙利裔人,幼年经历过纳粹德国的占领和匈牙利的共产制度。后来移居英国读书,现为美国移民。他早年师从英国自由主义哲学大师波普,深受其开放社会的理念所影响,曾经考虑从事哲学研究。他进入投资事业之后,除了在金融市场的表现大放异彩之外,更成立了一个开放社会基金,以慈善家的姿态,资助和推动在世界各地落实开放社会的理念。他还认为,他自己在金融市场上的成功,是直接受益于波柏的科学哲学。他认为他自己在金融市场的大风大浪中,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在于他以该波柏哲学的原理为戒,也就是人的认知的可错性(FALLIBILITY)。 不过索罗斯并没有把波柏的哲学作为教条来接受,他更认为、波柏的科学方法论是不能和他的社会观分割开来的。人的认知既不可能完美,理想的社会就只能是一个具开放性的社会,因为只有开放社会才会懂得如何纠正错误。索罗斯试图应用和继承的,正是波柏的开放社会这项实践上的价值,但他发觉他要这样做,就得批判地处理波柏的科学哲学。他认为波柏虽然发现了可错性观念,但却仅仅把可错性视为一个知识论命题,并以为可以由此重新建立关于科学的统一方法。但对索罗斯来说,可错性其实只是人类知识的不确定性质的其中一个面向,在这点上海森堡的量子力学发展的不确定原理,可能更靠近知识论上的极限(索罗斯将其创办的对冲基金命名为量子基金,更蕴含了对海森堡学说的敬意)。不过,索罗斯要提出的,是一个比知识极限更为重要的社会和历史命题:任何社会制度和人为建构都有着根本缺陷。在一九八七年出版的《金融炼金术》一书中,索罗斯简略地提出了他试图通过可错性,导引出一个实践行动的哲学和一个历史的理论。而转变的关键是他所提出的反射性观念(FEFLEXIVITY)。 反射性可以被表述为这样一条主张,亦即信念会改变现实。不过,参与改变,甚至塑造现实的,总是错误或有缺陷的信念。而现实也非恒定不动的现实,而是不断为错误的期望、认知所推进的现实。两者形成双向关系,但又互不对称,这就是索罗斯所说的反射性。它否定了超然客观知识的可能,并同时指出了思维和现实的互动性质。索罗斯认为他提出的反射性原理,最宜用来了解市场。因为所谓市场价格,并不只被动消极地反映价值,市场操作也并非朝向与现实一致的均衡,而是渗入了投资人的偏见、期望、反应、甚至情绪。在《金融炼金术》一书中,他以他在金融市场操作的实例,来说明他的反射性学说。他批评许多经济学理论,都将市场描绘为环绕一个均衡的状态运作,努力去认知其趋向。这项假设缺乏了对人类知识可惜性的意觉,也缺乏对认知作用和参与作用互相干预的了解。这些经济学理论大多以理性人作为前提,以为可以像自然科学一样,提出预测和解释的通则。但实际的情况却是,经济学理论,特别是金融市场上的理论,往往本身就不断参与着去改变市场的性质。例如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急速发展,是建立在有效市场论之上,但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滥觞,也可能一举拖垮市风 以金融市场来说,大部分关于金融市场的理论都相信金融市场和其它市场一样具备某种环绕均衡的规律,来说明各种金融工具的功能,而这个均衡点是由各种所谓基本因素所决定的。金融市场的摆动只是周期性地回应外来的震动,或者因发展而出现的暂时不平衡。然而,索罗斯的反射性观念,否定了金融市场上所谓基本因素的决定作用,因为金融投资活动本身正不断在改变因素价值。价格不只是基本因素的函数,也是投资活动本身的函数。所以,索罗斯所观察到的是大起大落的、只有短暂均衡的国际金融体系,它不单不是反映或者调节市场经济的工具,反而在不断的强化作用底下,成为例如是最近亚洲经济模式熔解的催化剂。 金融市场之具有这种吊诡的作用,在于货币是紧密地和信贷连接,而信贷本身就是一种反射现象。信贷的抵押品是授信的凭籍,但抵押品的价值本身又是受到信贷活动的影响。所以,离开了反射现象就不能了解货币。凯因斯学说和傅利曼的货币主义理论,都是以不同方式回避了反射现象。特别是后者,以为将着眼点放在稳定货币供应就可以稳定经济,但当前深重的国际金融危机,正好说明了忽视了反射作用就不能了解波动,尤其是国际间的金融波动。所以,所谓充分发展、无所不在的市场,并不会发挥神奇的不可见的手的作用去调节资源,达致合理的配置,因为均衡只是在有限范围内出现,市场的本性内含着的正是不均衡的大起大落。 事实上,按照索罗斯的反射性原理,对金融市场的批判,更隐含着对那些实际上助长了过去国际金融市场飞跃发展的金融理论家的批判。在新著《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一书中,索罗斯特别点出由诺图尔经济学奖得奖人创立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基金(LTCM)倒闭,说明他们所依恃的均衡理论并没有用,也说明理论认知是如何介人塑造认知无法完全把握的不均衡的现实。他早年的著作立意题为《金融炼金术》,就是对实证主义经济学,以及背后依赖的科学名气的反讽。他认为“炼金术”比“社会科学”一辞更少误导性,因为这更能说出错误的理论前提如何在不断塑造我们的历史。 很清楚,索罗斯实际上已脱离了波柏讨论可错性的原初题旨,他不再把可错性看成单纯是一项认识论上的缺陷,人们只要处理了它就能建立科学的知识。反射性的观念,导致索罗斯否定了建立完美社会知识的可能,以及实证主义的知识论和建基于它之上的科学观。在这个意义上,索罗斯和哈耶克同样持一种反科学主义的观点,也是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对极权社会制度同样都是深恶痛绝。不过,在构想一个与极权主义不同的社会时,索罗斯并没有依赖一种所谓“自生自发社会秩序”的观念,也没有把“自生自发社会秩序”理解为市场,而是提出一种实践性的怀疑精神和让批判性得以存在的开放社会观。而正是这一点导致他提出了和很多今日自称为波柏或哈耶克的追随者大异其趣的判断和结论。 在质疑任何社会制度和人为设计的大前提下,索罗斯要跨出比一般科学哲学更大的步伐。他放弃了波柏的试错法,他的反射性观念真实更靠近一种辩证关系。不过索罗斯认为,他的辩证观点是开放性的,非决定论的,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都有距离。他亦曾称他的理论为“鞋带理论”,以描述认识和现实的开放互动。他所关心的其实是思维和现实的双向回馈,不单是认知者的消极的认知功能,而是认知者的参与作用,从而超出知识论而到这一种建基于开放社会的价值判断,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观和历史观。 一九九二年,索罗斯一举击溃英格兰银行要努力维持留在欧洲汇率机制的决心,在投资界的名声更上一层楼。一九九六年,他出版了《索罗斯论索罗斯》一书,论及自身的成长、投资概念、人生哲学和政治观点,特别是他如何通过他创立的基金会介入一九八九年之后的东欧政治发展。在这部以访谈为内容的书中,他表示了对世界局势的忧虑。其时民族主义在俄罗斯和巴尔干半岛正取代共产主义而起,他觉察这背后兴起的实质上只是强盗资本主义。他抱怨西方国家对前苏联和后来俄罗斯的援助太少太迟,无法把握时机让苏联更有秩序地进行改革,或让解体后的前苏联社会走上开放社会的正轨。很显然,此时索罗斯心目之中实现开放社会的路径,仍然是以西方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为楷模,所谓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转变,也是理解为从东方到西方,从共产主义到自由民主的转化。在这点上,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理论,无可否认是脱胎自一种冷战话语。然而,我们只要耐心地从索罗斯的思想架构去解读他的政治立场,就会发觉他那个开放社会的概念工具,并不止于对共产主义的批判,而是遍及一切社会制度和人为建构,他力图摆脱那种非此即被、非黑即白的冷战思维,因为它本身就是封闭社会的意识形态,使人无法意识到任何人为建构的根本缺陷和可错性。 如果苏联东欧的经验对索罗斯曾经是封闭社会的典型,那么冷战后全球化的步伐随着市场万能论主导了世界经济体系,则已慢慢地孕育出封闭社会封闭思维的另一种形态。在他的最新著作《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一书中,索罗斯更直斥这种市场万能论为市场基本教义。虽然索罗斯无意否定市场和民主是开放社会的必要成分,但他觉察到对市场根本缺陷 的妄顾,已使市场基本教义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最大危害,也成为实现开放社会的最大障碍。在索罗斯眼中,当前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只是一个扭曲了的开放社会,它实质上是一个抽象的帝国,它有着它的中心和边陲,中心提供资本,边陲使用资本。但游戏规则只有利于中心,跨国公司既可以往低税、管制少的地方无限游移,国际金融投资组合就更具有无限的弹性。虽然这个体系是由表现在资本、债务和货币环节上的不对称关系所主宰,但却有一个根源于完全竞争理论的意识形态在支持着它。市场基本教义对放任市场的盲目信仰,是建基于市场机制趋向均衡,而均衡亦即资源的最优配置这项假设。 信仰市场基本教义者,就好像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所声称体现的科学真理,达到了完美和绝对。然而,索罗斯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封闭的思维,他门所不能认识的,正是市场的根本缺陷,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的根本缺陷。市场基本教义的危害,在于它妨碍社会改错机刻的建立,甚至侵蚀原有的议会民主。 对于亚洲金融风暴,索罗斯实际上并没有像一些自由主义的市场基本教义派一样,单纯把问题归咎于千疮百孔的所谓亚洲价值裙带资本主义、官商勾结等令所谓完美市场不能实现的外因,而是在承认这些现象的同时,又指出在这些现象背后的,是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和它内在的不稳定性,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的角色,衍生性金融商品和各种基金的作用等。 索罗斯的这些批判,一方面是要指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如何依靠一些明显地具有缺陷的理论,同时亦指出依据这些有缺陷的理论所设计出来的人为制度,如何无力解决自己参与制造出来的问题。从这个最根本的质疑开始,索罗斯带出他对全球化现象的宏观诊断,也就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前提下,人类却缺乏一个有效的全球政治架构,以及一个真正的全球社会。如果资本主义和民主在中心国有历史的关联是事实的活,当前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却没有推动朝向民主的力量。因为市场基本教义构想出来的全球市场,并不内含一个有效的民主改错机制。这归根到底是因为这种全球化是统一在一种单一的市场价值之上,忽略了其他社会价值。索罗斯更夫子自道地指出,自已在投资活动当中并不能顾及赚钱之外的事情,因为市场价值对市场参与者来说总是至高无上的,他的对手只是无名的市场。不过这没有妨碍索罗斯本人去明白,只有社会价值和公众利益的考虑,才足以制定监管市场的规则。当前经济波动和危机的起因,正是缺少了这些规则。 可以说,索罗斯的思考,归根结底还是价值的问题。为市场基本教义支配的经济学,其错误不单在于漠视了在认知上可能犯错,而是使市场价值入侵了它不应存在的层面,以及封闭了不同价值之间的相互反馈。也就是说,缺乏了以反省(反射的另译)的角度去看待价值同题。在这情况下,我们有由单纯的市场价值所推动的寻利行为,却无任何开放的社会空间去让其他社会价值为市场设立规则。索罗斯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一书中,不无感慨地抒发他对社会价值失落的感慨。他回忆祖国匈牙利在纳粹时期,人民姑息对犹太人的迫害。二十年后重回旧地,人民对政治压迫却高度敏感。虽然大部分人选择找寻妥协安身之道,但对拒绝妥协的人仍视之为英雄。然而这种明辨是非的意识却在变天之后的匈牙利开始消失。显然,新出现的民主体制并不敌市场自利价值的磨性。 索罗斯自身为举足轻重的国际金融投机者,却又坦白而彻底地批评全球市场,足见在实践上,索罗斯是一名非常自觉的反讽主义者(IRONIST)。而从思想脉络看来索罗斯所代表的,是一种坚持道德警觉的自由主义。他的新书《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曾请英国力倡“第三条道路”的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意见,深研自由主义的哲学家格雷〔JOHN GRAY)指引过他重读卡尔·布兰尼〔KARL POLANYI〕的《巨变》(GREAT TRANSFORMATION)。在他这本副题为“岌岌可危的开放社会”的新书中,他不时援引一些政治哲学上社群主义学派前概念,例如桑德尔(M,SANDEL)的“有负载的个体”观念,就被索罗斯用来批判启蒙运动那种空洞抽象的个体观。在“开放社会”一章中,他又谈到对西方社会的失望,因为那里只把开放社会、自由民主当作宣传。他更明白地修正了以前把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对立起来的做法。因为他最新的恩考架构使他意识到:开放社会纵然是惟一的普遍性理念,但它无时不面临一种危险,即把它看成某种非此即被的逻辑结论,而这反而是一种封闭思维的结果。事实上,他认为当前开放社会正面临着包括市场基本教义的各种极端主义的威胁。 当今世界上,能够声称自己比索罗斯真正了解所谓“成熟的市场社会”,终日泡浸在全球资本主义这个无穷丰富的现实世界的,相信还多的是。但要像素罗斯一样能和这种体制的“基本事实”,也就是世界性市场每天的运作打交道,以市场的密切的参与者的身份亲身进行实证研究,而又兼具价值反思能力的思想家,世上却没有多少人。的确,如果要找市场关系最为成熟,也最为抽象的形态,莫过于今日力量达全球的金融市场,问题不在于那些领导这些市场力量的地方目前是否最能容让自由精神发挥,而是在于透过全球资本主义存在的这项基本事实的中介,世界能否过渡往自由王国,人的思考状态是封闭还是开放。索罗斯驰骋世界金融市场,坐拥亿万,却仍以“失败的哲学家”自称,关键乃在他具备一种对自由价值根深蒂固的执著,而非满足于以自由主义装扮骨子里的封闭心智。笔者相信,如果缺乏了对作为一种核心道德价值的自由主义的这种了解,我们实难以明白索罗斯从何可以守护波柏的开放社会理想,而又会勇于尝试从黑格尔、马克思等历史阶段论的迷雾中拯救出辩证思维的精髓(常见的倒反是以自由主义为表,历史目的论为里),从可错性的波涛澎湃中顿悟反射的历史,体正历史的反射(反省),从市场的基本教义中解脱。毕竟,在全球化的新阶段以大风大浪的方式已逼近眉睫的今日,划出一个所谓成熟的市场社会以和“我们的生活世界”相对,这种区分本身就并非一项无可争议的基本事实。在“广信”倒闭、“红筹”暴跌中严重失利的港资、外资银行,以致小股民,就深明基本事实不是以这些范畴来描绘。以为有外于全球化这基本语境的亚洲模式和亚洲经验,又或者想绕过全球资本主义及其危机这基本现实来构想开放与自由,是不是缘本求鱼呢? 要求索罗斯本人来提供实现开放社会的蓝图,或者逃出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困境的药方,似乎有点异想天开。他提出的真正全球政治架构及全球社会。与其说是一条出路,不如说是一项问题和挑战。但至少,在当前死抱各种主义和标签的基本教义和封闭心智,还是不断在改头换面,以捍卫正确路线,治国良方的姿态出现的情况下,以人类可错性的成戒条及心情来阅读这位不知应归类为右派还是左派,香港人称之为“金融怪杰”的索罗斯,想还是有助于在暴风眼中的一点反省吧。 摘自《读书》杂志1999年第5期
|
| 返回 |